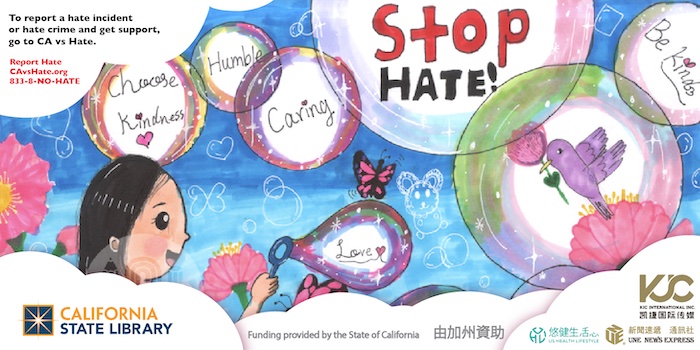每当感觉内心特别空旷的时候,就拚命翻书,像是找止痛药一样,想从一些语句中来找一些支撑。 这次一口气看了数位老先生评说【红楼梦】:周汝昌、王蒙、刘心武、白先勇、蒋勋。
其实,无论考证了多少个版本,运用多么完善的推断,他们无非都在用力向世人证明自己一些过人的见解与学识而已。这其中,只有白先勇的一句话打动了我:“【红楼梦】不过是曹雪芹的追忆逝水年华。”从生活经历上来讲,只有白先勇与曹雪芹的生活经历有相类之处,看过繁华盛景,历经惶惑飘摇,人生况味,总在欲语还休之间,所以他算是比较能够体会作者的心境。
在大学时读【追忆逝水年华】,全然不记得内容。但是那种旧帘幕后带着深院气味的叙事方式,令我低徊不已。从那时起,我就梦想生命中有一天,能够如普鲁斯特一样,什么都放开手,只是躺在厚厚的窗帘后,追忆一些可有可无的旧事。
我以为,文学的最高境界,是在不着痕迹处。一旦有了目的,动了心机,都要大打折扣。被称作法国“百科全书”的大作家巴尔扎克,一生著作等身,简直写尽了人间悲喜剧。可是他死前说过一句话:“其实我这一生,一直希望写的,是一本无所谓的书。”可终其一生,巴尔扎克都没有完成这个愿望。这令我想起他在【欧也妮 葛朗台】中的最后一句话:“欧也妮,一个天生的贤妻良母,却即没有丈夫,也没有孩子。” 若心有戚戚,自会明白作者的深意。
我的弟弟在名校文学院任教。他曾对我说:“你早年写的诗,如果与席慕容、舒婷的放在一起,也是有亮点的。可惜你没有好好经营,才华横溢,洒了一地。我的文字,都是用来赚钱的。”听了这话,我低头无语,充满愧疚。只是心中执拗地、弱弱地升起反驳:“可是我好不容易不用拿我的文字来赚钱了。” 唉,教授弟弟,我岂没有骑着自行车,在北京的严冬里,来往于各个编辑部中间,送稿子赚稿费的昨天呢?如今可以不必绞尽脑汁去撰稿,虽然少有产出,但至少对得起我心目中最神圣的文学了。中国有句话“著书都为稻粱谋”,真觉得这是文人最大的悲哀。人生不如意事,十有八九。巴尔扎克都做不到,又有几个人能够真正做到?
当然历史上是有过这样的时代的,比如说中国唐代。那个时代是养文人的。李白自不必说,他囊中少钱,竟还有五花马千金裘去换美酒,想来过着阔绰的生活。杜甫住着草堂,风雨飘摇,但还有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、“夜雨剪春韭”这样的生活状态,该是小康吧。就连诗鬼李贺,说是最后穷愁潦倒而死。可是在他最穷困的时候,却还能骑巨驴,后面跟个小童,在外面闲逛觅诗。包括曹雪芹,他虽然到了举家食粥的地步,但毕竟贵族出身,尚有可以花费十年功夫来写一部小说的余力。所以一如普鲁斯特,这些人在写作上,在很大程度上,是可以任性的。小时候,红楼这样的书,被称为是“闲书”,如果有一个下午什么都不做,只是读红楼,那就感觉相当奢侈。所以无所谓的书,只适合无所谓的人读。普鲁斯特、曹雪芹、白先勇们的逝水年华,谁解其中味呢?
在生活的重捶之下,人们用各种砺志与心灵鸡汤来充塞与壮大自己,说着说着,最后连自己都信了。忘记什么人讲过,红楼梦中的女儿们,薛宝钗是目的论者,林黛玉是表演论者。宝钗为了达到目的,可以不计较过程。而黛玉,则注重过程中的细节,而不问前程。到底哪一种人生比较完美?见仁见智吧。有些事情,你明明知道如何做更符合生存的利益法则,却偏偏不去做,或者做不到。目的性太强的事,于我,是非常难以做到。落得个晚景凄凉,做上了少奶奶又如何?我倒真希望如黛玉一样,将自己的眼泪与诗心,全都牵牵绊绊地消磨在路上。
说到这里有些跑了题,其实我想说的是,纵然不愿意承认,可人生本就如逝水,一切都是虚空与捕风,与其花费心机去成就什么,不如放开手去追随本心。世间万物,高明莫过于随节气而荣枯,随浪波而逐流。每个人或多或少,或早或晚,都要完全面对一个追忆逝水年华的终了。人一生终究是在普世价值中载沉载浮而归于湮灭,什么才算是一个笃定的远大前程?表演得再好,总有谢幕的时候;表现得再坚强,总会有崩溃的时候。也许许多注满正能量的心灵非常蔑视这样的悲音。可是,悲哀、忧郁、绝望,却恰是人生的底牌,是成就你内心的力量。人生之幸,莫过于成就了自己的执念。
加缪的墓志铭是他自己的名言:“在这里我知道了什么叫荣光,那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”。这位英年早逝的哲学家的名句,道尽了所有珍惜内心的人的任性。人心即如幼树,总要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修剪枝叉,只是,在欲望的枝柯疯长的时候,多少人能够看得清,哪一枝是主干呢? 我也一样地困惑过,着急过,错砍了多少青葱的岁月呵。真的到了能够不急不徐的境界,是要经过多少的烟雨迷途呢?
爱了这么多年的文学,终于明白原来自己不过是一个读者。每一件事情,都有一个很高的门槛,如果感觉很容易就能迈过去,那不是因为你多么有才华,而是你容易相信错觉。越是让我仰视的东西,越让我畏惧。害怕一不小心在我的手上打碎了,就是万劫不复。许多人一生中都没有读过一遍【红楼梦】,也有人用一生的时间来研究这门学问,更多的是如我一样略知一二的看客。我们爱过许多故事,许多东西,许多人,只是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害怕,也有同样易碎的东西,一个人深深地、小心地珍藏着。
近来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学京剧,字头、字腹、字尾;西皮、二黄、四平调。本就不专业,也无须有表演的压力,慢慢地体会,慢慢地学唱,就如小时候在葡萄架下读红楼,不知时间流逝,也不问身在何处。在这样的学习与练习中,我渐渐沉下心来,找到了我的速度与安全感。也许今生写不出一本无所谓的书,但是可以唱一段不上演的戏吧。我在京剧中几乎找到了所有我需要的好东西:文学的、音乐的、美术的、形体的,如此繁杂与深不可测,如此迤逦与精妙绝伦。
“劝君王饮酒听虞歌,解君忧闷舞婆娑。赢秦无道把江山破,英雄四路起干戈。自古常言不欺我,成败兴亡一刹那。”跟着老师的胡琴,我摸索着寻找温柔的高音区,感觉着古战场的清泠月色,慢慢松开紧扣的双手,让生命的珍宝释放出来。此刻,“林黛玉焚稿断痴情”的任性,虞姬“大王意气尽,贱妾何独生”的任性,似蝴蝶翩跹,如余音绕梁,在美利坚西海岸的夜潮中,向死而生。
(刘茁 2017年荷月 圣迪玛斯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