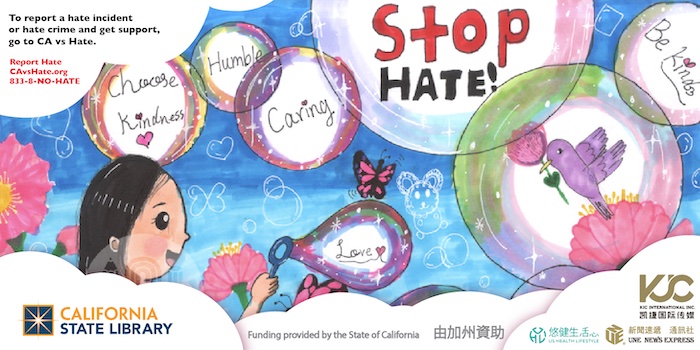刘茁
原先以为漂泊是一件浪漫的事。很诗意的两个字啊,仿佛就是背着行囊,走在方砖路上。后来才知道,漂泊其实是你弄丢了自己的时候。是你只用脑思考不用心思考的时候,是你只有野心没有激情的时候。是干燥的风从四面吹向你,让灵性风干、剥落,让你变成一粒砂,混入无边的沙漠。
2015年12月圣诞节,又一次到夏威夷旅行,在那时,做出了人生中又一个重要决定。其实,那一刻的放松,犹如大战前夕深不可测的宁静,令人充满期望与惶恐。可我就是宁愿面对一个不确定的未知,也定意要放弃已经揭晓答案的舒服区域。哲人说,性格即宿命。今天看来,此言不虚。似乎一直都在追求稳妥,却一直都在放弃已经到手的平静。我不喜欢跑步,不喜欢做重复动作,也不能够忍受日子重复日子。
瓦胡岛上的火山口,叫做钻石头。最后一次喷发是二十万年前。不爱登山的我,穿着人字托儿,一口气登上770英尺的山顶,只为体验一下,人有多渺小。火山口芳草萋萋,强风烈烈,前无古人,后有来者,波撼岳阳城,气蒸云梦泽。在造化奇巧面前,所有的江郎都会才尽,因为青山绿草,敦厚的热带云,永远静默地在那里,从不在乎谁的赞美或者眼泪。
登临也是一种境界。中国古人讲究这个。鸢飞戾天者,望峰息心;经纶事务者,窥谷忘返。更何况这座山峰之下,是更大的主宰,无边的海洋。而海洋与青峰之外呢?波利尼西亚人把天地称作父母,赐予人类所需的水果与雨水。他们认为人不应该去征服自然,尝试这样做就已经很愚蠢。在这里,人们应该是赤脚走在沙地上的,草席一片即可棲身,茅屋一檐可避风雨。女人无需涂脂抹粉,鬓间一朵木槿花,身着一片手织布,已是极美。任何人工的东西在此都显得碍眼。这一切都一如18 年前的旧风光,引我走到回归本真的绿色小经。
然而威基基海边多了许多高楼与塔吊,奢侈品牌店铺栉比。夏威夷本地人在通向山间的路上,立了牌子反对城市开发,反对城市文明。我从洛杉矶的楼宇中暂时逃向这里,却一样地感受到城市文明给这伊甸园带来的刺痛。我们一定都要如此漂泊吗?这里是我心灵的故乡啊,是我孤独的避难所– 一座湿润的、天堂般的绿色岛屿。我多么希望自己安静下来,在这座孤独的岛屿上,慢慢储存起盈盈的水份。无论世界多么荒凉,心中一定要让阔叶木的森林生长,一定要有自己的雨水、彩虹,与大海。在告别夏威夷的前夜,我再一次跟上穿草裙的塔西堤姑娘,一一去点燃,入夜的火把。我希望以这种仪式感,为人生的结点,做一个脚注 — 又要开始漂泊,然而我停留过。
小时候,父母将我们姐弟三人送到乡下奶奶家。乡下的日子非常无聊,尤其是夏天的午后,时间特别的漫长,人们都在午睡,母鸡偶尔“各各大”地叫两声,那种时钟几乎停摆的感觉,让我如坐针毡。有一次我竟大哭起来。奶奶为了哄我,就带我们到村子口去看汽车,看看是否父母亲会突然回来。虽然从来也没有等到父母的汽车回来,可是每次到了村口,我就高兴起来,就觉着那条不见尽头的柏油马路充满了希望。
每一天清晨阳光照进屋子,我也会陡然高兴起来,就觉着这一天或许会发生许多有趣的、令人惊喜的事。也喜欢每天傍晚时分,炊烟袅袅,或许我的父亲会突然推开大门赶回家来。那时候也就3、5岁的样子,那无聊的午后与充满希望的黄昏与清晨,深深地印成了我的意境。

此后经年,又是一番不同的人生景象,忙碌与漂泊感,让我开始怀念起童年那些时间静止的午后。或许我们害怕重复,却恰恰是在重复。在飞机上无聊,看“我不是潘金莲”,起初感觉导演真是太差,拍了这么一个反反复复疯女人的电影。后来却突然悟到, 这就是我,或者是我们。每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执念中而不自知。有了红玫瑰,喜欢白玫瑰;有了蜗居,又想着远方。真真天下之大,竟没个安排处了。
威基基海滩上斜阳依旧,20万年,距离下一座火山,人类还有多远的路未曾行走?其实经历的风浪多了,心就不惊了。岁月总会慢慢告诉你:童年的夏天从不曾走远,今日的盼望,依旧是当日的盼望。放下执念,一切都是风轻云淡。山河未改,只是心动。
( 2015 年12月26 日 于檀香山 2017年9月洛杉矶又及)
本網站內容嚴禁未經授權轉載、複製。本網站僅為一般訊息平台,所發內容不代表本站立場,不構成任何投資、購買、要約等建議,不對資料之完整性、精確性等作任何保證。